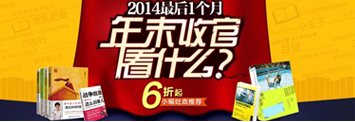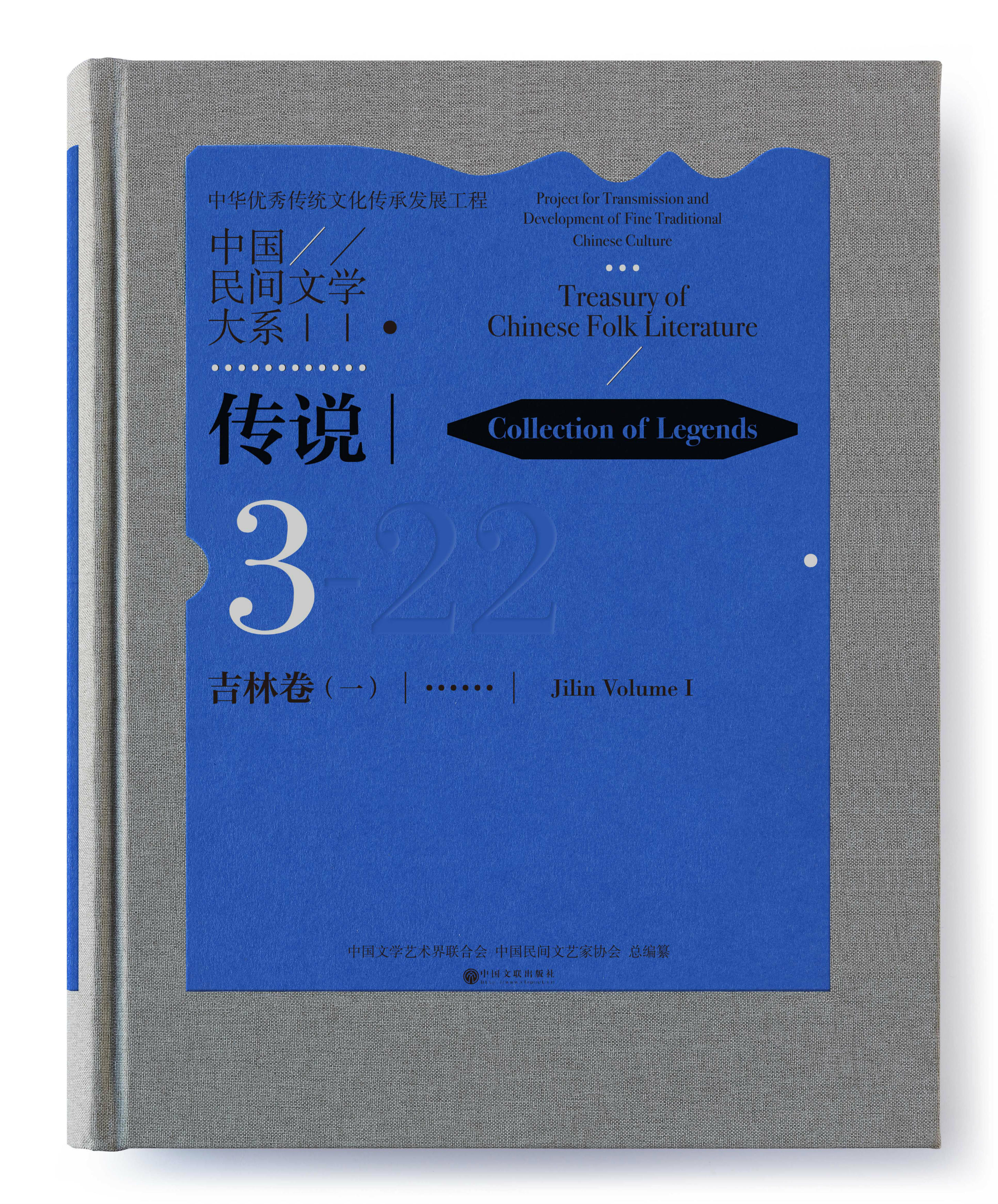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吉林卷(一) 》是由中国文联负责组织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 “民间传说”卷的示范卷,由曹保明担任主编,其中包含三百多则流传在吉林省各地的人物传说与风物传说文本(含异文) ,涉及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多个民族,反映了吉林的社会历史、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与物产资源,表现了吉林各族民众的生存智慧、生产经验,以及他们的理想与信念、思想与情感等,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该书所选传说文本涉及内容相当广泛,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其中很多文本都表现了一种共同的道德理想—— “牺牲自己,成就他人” ,我们可以将这一类传说文本称为“牺牲叙事” 。牺牲叙事尤其密集地出现在风物传说类别下的山川传说中。吉林境内多山水,著名的比如长白山、天池、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当然还有更多的山水之名是我们这些外省人不熟悉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世代吉林民众生息繁衍的家园。但无论多么秀美的山峰,多么清澈的河流,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时期,都可能成为吉林先民生产生活中的障碍。比如水患,比如山间猛兽。吉林先民曾想方设法与这些障碍进行斗争,他们中一定产生了不少英雄人物,也一定存在很多牺牲,而记录这些英雄事迹的口头叙事在传承过程中增加了诸多神奇的情节,逐渐演变为牺牲叙事。
这一类传说相当多,比如《老龙湾》《金线泉》 《黑鱼泡之一》 《查干湖》 《天池水和浮石》 《避风石》 《补天石》 《鸡冠砬子》 《七星连珠岭》等。在这些传说中,都有一个或数个英勇无畏的主人公,他们为了乡亲父老,与自然灾害或妖怪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却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以《老龙湾》为例,传说这样讲述:龙湾一带出现了一只伤害百姓的龙头怪兽,三兄弟自告奋勇要为民除害。他们虽然英勇,却难敌怪兽,在危难之际,他们受到人参仙女的帮助,战胜了怪兽,自己也化身为三座山峰守护着故乡的安宁。吉林传说中集中出现这么多“牺牲自我,成就他人”的牺牲叙事,既与吉林多山多水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客观生存困境有关,又与先民和困难抗争的群体记忆有关,更是先民共同的道德理想的反映。
牺牲叙事中反映的道德理想其实是对中华传统道德理想的继承。在早期神话与传说中,我们随处可见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伟大牺牲和奉献,比如:女娲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采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为了控制洪水,鲧盗取天帝的息壤而被处死;为了将民众从茹毛饮血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商伯冒险将火种带到人间。这些神人、氏族领袖与氏族英雄们为了民众和后代毫不迟疑地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这种牺牲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最重要、最高尚的道德理想之一。也正因为有了从盘古到鲧、禹等许许多多祖先的英勇牺牲和奉献,才有了绵延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和无数华夏儿女的生息繁衍。
有意思的是,在吉林传说中“牺牲自己,成就他人”的主角最后往往化身为山川,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比如《查干湖》的主人公查干少布为了拯救草原的旱灾,吞下仙丹化身为湖泊; 《天池水和浮石》的两位主人公玉柱和天柱为长白山百姓挖出了天池,自己却累死了,死后化为玉柱峰与天柱峰; 《避风石》的主人公毕峰为了解决家乡的风灾化身为一块避风石; 《补天石》的主人公刘仁智为了镇压天池中为害的黑龙,化作了一块石头。除了化身为山川之外,还有主人公化身为动植物,如《凤凰岭》的主人公化身为鸟, 《寒葱岭》的主人公化身为植物寒葱, 《母鹿梁子山》的主人公化身为鹿。
这样的情节似曾相识。 《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载:“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肤为田土,发訾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 ”盘古化身万物之后,先民将自然万物等同于盘古,由此产生了盘古崇拜。直到当代,还有不少地方的民众存在这样的盘古崇拜意识,他们认为晴天的出现是因为盘古爷高兴,而阴天的出现则代表盘古爷生气。在盘古身化万物的情节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牺牲自我,成就世界”的道德理想,更发现了早期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即人与自然可以合而为一。
早期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与后来哲学上的天人合一观念不同,它是在原始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的产物。而吉林传说中主人公化身为山川、鸟兽的情节,其实是对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的继承。当然,化身为自然物的情节在吉林传说中的集中出现还有其特殊的地方性原因,比如以萨满教为代表的较为原始的宗教信仰在吉林保存得较好。与后来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相比,早期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其实更可贵。天人合一,不仅意味着人和自然可以合二为一,更代表了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正如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中所描述的那样:与盘古从同一颗蛋里一同诞生的还有清气和浊气形成的天地自然。既然人与自然共同被孕育出来,那么人类更应当尊重自然、善待自然。
也就是说,在牺牲叙事中实际上含有对两种基本关系的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牺牲叙事认为应该“牺牲自我,成就他人” ;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牺牲叙事认为应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以上两种思考即使今天看来都是非常可贵和先进的。了解了前人的这两种思考,我们也更能体会当前整理、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传说”组专家)